仁一度怀疑自己有青光眼,因为总嫌别人目光刺眼;也怀疑有风湿病,风吹草动就关节作痛;也怀疑耳鸣,闲言碎语听起来震耳欲聋;心脏病也有,一受刺激就阵阵绞痛;泪腺有毛病,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打开阀门。且疾病随着年龄指数增长,而当仁躺在医院轰隆作响的机器下,却总出来健康轻快的指标。
“可我确确实实备受病痛折磨呀!”
“哪里不舒服呢?”
“头,眼睛,耳朵,鼻子,脖子……”
医生难掩嘲弄之色,“那你去看看精神病吧。”仁从他用白大褂裹住的胸腔里听到这样的声音。
如此以来,仁只好孤军奋战,寻找身体异样之源。直到有一天,她突然意识这疼痛的事实其实很明显、但正是因为事实太明显才视而不见——仁的头上多出了三根天线。
“信号接收太过敏锐。”
她重重的在厚厚的个人病历上写下。
为了远离这生命难以承受之敏锐,仁打算将它们麻醉掉。可它们不像多余的肉体,可以单独麻醉——甚至于切除也能活命,确切地说,不属于肉质身体,而是一种神经,与自己之关系如中国土地主权般神圣不可分割。
那就麻醉全部的我吧!仁想,肯定会有人笑自己小题大做,为了三根天线就要把自己变成木头?面对这样地嘲弄,仁不由得愤愤,这就是你们同理心不够了,为了不变成自怨自艾的讨厌角色,仁不愿多叙苦楚,可并不代表静默的背后就能少些辛酸。
仁尝试麻痹自己,无奈她作风太良好,硬麻醉不行,喝不下酒、抽不得烟;软麻醉不灵,游戏不上瘾、看剧不迷恋。而强行闭目塞听,则导致仁清醒地过着浑浊的生活,行尸走肉却扛着个常人的脑子,良心不堪重负。
退一步的痴呆不成,便求进一步地疯狂。但经过长期地尝试,仁既没在学术上废寝忘食,也从未为艺术通宵达旦,往往没摸清门道便兴味索然。仁开始为自己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疯子悲痛不已。人说仁你悲痛个啥呢,这不是没事找事吗,非得成个精神病才满足?
进退两难,仁欲求于恶。杀人如麻的洒脱匪气令她欣羡不已、心神激荡,一旦如此,十根天线又能怎样?对仁来说,害命不为谋财,只是图一种突破体系地释放。可这比前文更不靠谱,即使不去杀人,变坏对仁来说就足够夸张。仁悲哀地发现,她什么都有,却也什么都没有,她有亲人间地牵挂,这让她没法浪迹天涯,父母不打姐妹不笑话,同事不差领导不压榨,她喘不过气却没人逼她,遍体鳞伤却没人伤她,她找不到倾泻口,找不到罪魁祸首,连个和生活翻脸的机会都没有,一旦成了阶下囚,没有作案动机的她,就连对簿公堂都不知如何作答。
“仁某,家庭情况如实道来!”
“回禀大人,小的父母健在,尊师重教,家庭和睦,兄友弟恭。”
这没一点猛料的介绍怕是大人要拍板喊声放肆,对仁的悲惨经历翘首以盼的一众人等也得大失所望。做贼既无缘由,便也成不了气候。
不成气候…唉,仁在这边施麻醉之术,天线却更热烈地接收着信号,噼里啪啦,恨不得放出电的火花。然而不同以往的是,这次接收到是心底的声音,心脏挤压出的悲伤情绪被天线接收,再传达到心脏使之绞痛,自产自销,自给自足,自成一体,自作自受。
“你在拧巴什么呢?”
仁毫不怜惜地大力敲击心口处,像个捶胸顿足的猩猩,出于本能或是无能。天知道她在想什么,她是懒得跑步而去盼望拥有断腿的那种人,要说原因,不就是图个良心舒服,浑浑噩噩却心安理得,坏事做尽却心平气和,成为那种可以放弃梦想、不怀希望,却问心无愧的人。
“不可能呀。”仁的心悲伤地说。
天线总让她聆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,无情的外界批评、贪婪的内心期望;逼她直视千奇百怪的眼睛,自己的迷茫眼神、他人的不屑目光;让她迎接猛烈的风,吹的她晕头晕脑、迷失方向;让她听到心底的呐喊,像溺水的鱼一样。
它喊到:“叛徒和胆小鬼。”
“你闭嘴。”仁疲劳地回应它,泄气一般爬上床,想进入睡眠,天线却还在吸收四面八方的光,仁紧紧阖上眼皮,它们却涌入脑壳,一时亮如白昼,刺痛难忍。给我黑暗吧,仁咬着牙想,假如给我三天黑暗,能把花花世界洗涮个干净的黑暗,天线在这黑暗里效力全无,而我则能像个婴儿一样酣睡一场,梦里空空荡荡,醒时清清爽爽,平日里只需间或一轮自己的眼珠,那空洞的眼珠什么都看不到,既然看不到,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,没有不肯放手的物质享受,更没有苦心经营的精神追求。多好啊,这黑暗。
于是最后仁把自己逼进绝路,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黑暗。但她并没有收获到预想的幸福,仁想起当年“假如给我三天黑暗”幼稚设想,在那些孩子气的举动背后,是她没明白,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呼之即来,挥之即去,疯狂不是,麻木不是,黑暗更不是,黑暗既然能冲刷一切,她便不能忽视它冲刷自己的可能性。如今,被冲刷的仁逐渐了失去性格与面貌,一张河床那样,被冲刷得干净、平滑、一无所有,她坐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,偶尔想起以前的事情,这些事情像黑暗中闪光的碎片,一开始,她那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对这闪光颇感不适,甚至让她闷闷不乐,她毫不犹豫地驱赶它们就像驱赶眼里的沙子。很久以后,她才开始对这些小小的碎片萌生兴趣,捂着眼睛慢慢靠近,却发现碎片里映照着她曾经追求过的东西,她愚蠢的幻想和空虚的梦,碎片亮晶晶的,她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,直到长时间地注视让她情难自抑,涌出泪水,然后灌满她干涸的眼眶。
仁开始疯狂地思念起同样亮晶晶的光明来。
于是她呼唤曾经痛恨的天线,她曾经用尽心思把它们麻木掉,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它们的意义,它们是世界的入口和心灵的出口,她如此渴望听到那噼里啪啦的声音,以至于她的声音充满绝望和急切。可她的天线早就在黑暗地浸泡里彻底丧失了活力与热情,在黑暗里缩成一团,麻木到一碰就断。那时候仁明白了一个道理:一切道理都是在不可挽回的境地里领悟的。
仁是被自己的哭声吵醒的,刚刚一通胡思乱想,竟然睡着了。她惊魂甫定,僵直地躺在床上,直到她意识到自己正沐浴在白净的光线中,肌肉才开始一块接一块地放松下来。
仁对她的心说:“我刚刚梦到了黑暗。”
“感觉怎么样?”心问。
“它很像叶公的龙。”
然后仁坐起身,摸向头顶的天线,太好了,它们精神得很,它们是仁生活里的敏锐触角,只有仁足够勇敢,才能真正地爱上它们,爱上它们所揭示的真相。也只有闻风丧胆的胆小鬼,才会把仅存的勇气都拿来做叛徒,试图斩杀直面现实的可能,对自己孤军奋战的天线倒戈相向。
“最近她怎么样了呢?”我好奇的问。
“仁开始追求那些闪光的碎片了。”她的心快活的说,“虽然她曾经是个叛徒和胆小鬼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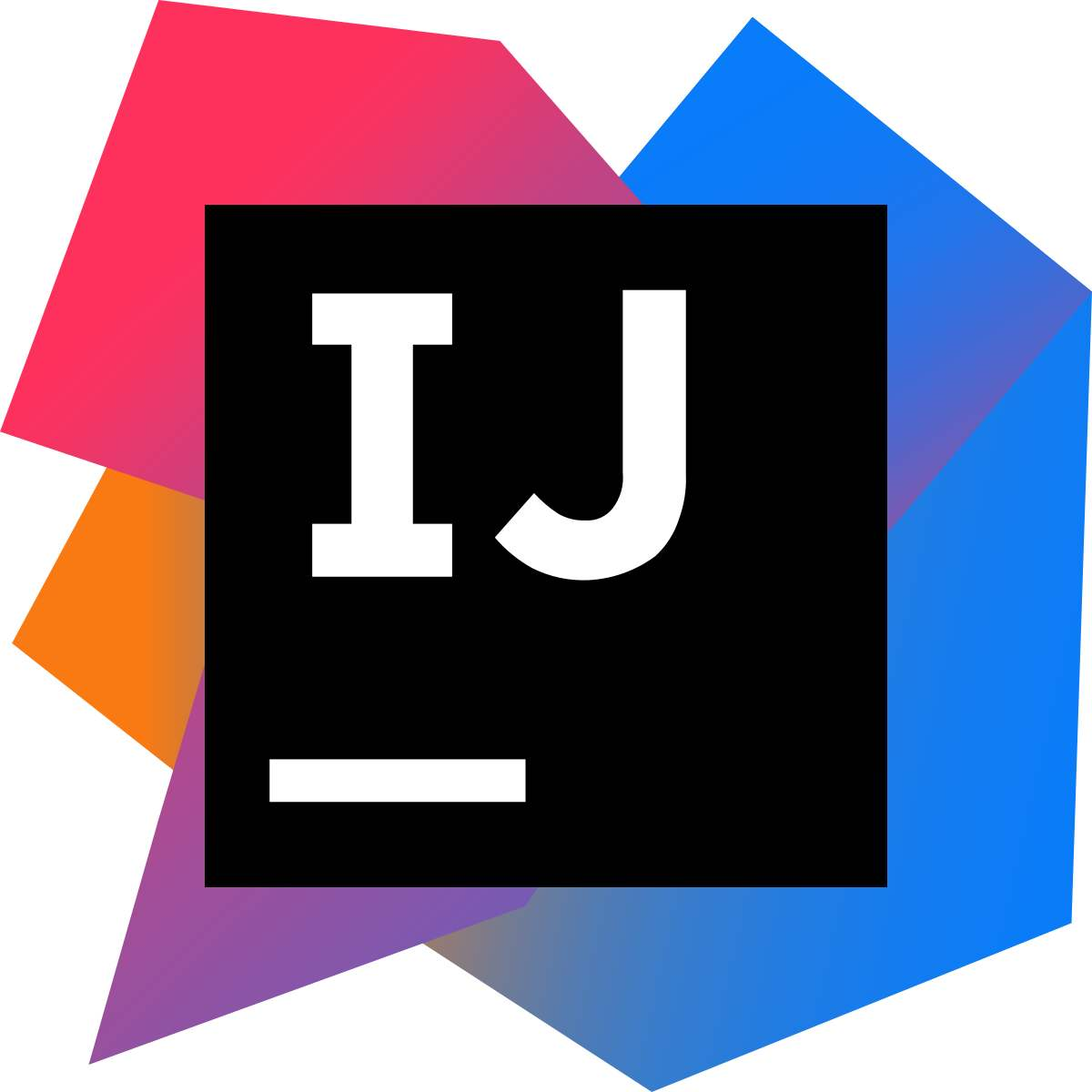



近期评论